前几天,Nature 官网发布了 Working Scientist 系列播客的第一期,召集了几位正在从事一线科研工作的科研人,讨论研究生在选择实验室的时候最应当考虑的关键因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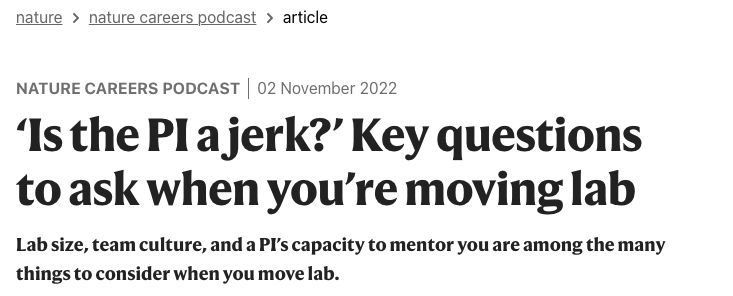
图源|nature
关于讨论的结果,Nature 已经简单粗暴地写在了标题里——选择实验室最关键的一条:判断你的导师是不是个混蛋!
在开始介绍这篇讨论之前,我们先来听一个和 jerk 有关的故事:
人生岔路,恶导当前
翁顺砚,现任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和彩虹室内乐团的中提琴首席,同时也在从事小提琴与中提琴的演奏教学工作;其于 2021 年编写的《舍夫契克小提琴协奏曲名作演奏指导》在各大网购平台皆可搜到。

这样的履历和成就,显然是个再标准不过的音乐家;不过,翁顺砚还有着另一重身份:
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了 14 年生物学的遗传学博士。
就像大部分中国学子一样,即便翁顺砚从小就热爱音乐,他也未曾真正想到过把音乐纳入自己的人生规划。
在翁顺砚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时,正赶上克隆羊「多莉」横空出世的 1996 年。「那正是生物学吹得很热的时候,人人都在谈论克隆羊。好像选了生物,前途就会一片光明。」
就这样,成绩优异的他选择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生物学专业。从本科到硕士,从硕士再到博士;翁顺砚曾经多次质疑过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方向。他觉得,自己充满跳跃和发散性的思维更适合从事文艺方面的工作,严谨的科学研究并不是他喜欢的。
也许是自己还没发现生物之美吧?本着一条路走到底的信念感和较强的个人能力,翁顺砚选择了坚持下去。
在不断的质疑和反思中前行,似乎是所有科研人的共性。凭借翁顺砚的能力和背景,若是想在科研领域继续走下去,即便「不喜欢」也肯定是「有机会」的。
但恰恰是一段出国交换的经历,彻底摧毁了翁顺砚从事科研工作的念头。
在翁顺砚读到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,他得到了前往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学中心进行交换学习的机会。但很不幸,这个实验室的导师是一位极其苛刻的华人教授——
也正是从这里开始,翁顺砚的科研理想彻底崩塌了。
 图源|精英说 翁顺砚在美国交换学习时的实验室
图源|精英说 翁顺砚在美国交换学习时的实验室
从翁顺砚来到实验室起,这位教授不断地给还是硕士研究生的他布置无数「不可能完成」的任务。
翁顺砚还清晰地记得,某天导师要求他独自完成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实验,并且不允许他查阅任何资料或求助同门师兄师姐。
他硬着头皮往下做,得到的结果自然是一塌糊涂;导师见状,不但没有提供指导或帮助,还直接对他进行谩骂,羞辱他「愚蠢」、「像猪一样笨」。

图源|精英说 翁顺砚和在美国交换学习时的同学们在一块儿
随着时间推移,翁顺砚逐渐明白,实验室里的同学们早就习惯了这位华人导师动辄拍桌辱骂,乃至恐吓威胁学生的作风。
在这种极端绝望的环境下,翁顺砚偶然重拾了对音乐的热爱。在辛辛那提大学交响乐团,他靠拉小提琴舒缓自己每天在实验室所经历的痛苦,并在这里结识了志同道合的音乐家们。
朋友们说,发生在实验室的一切是违法的,可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他。

图源|精英说 翁顺砚和朋友一起演奏乐曲
所幸,在音乐和友情的帮助下,翁顺砚完成了这段学业。「如果没有他们时时拉我一把,我在美国的情况可能会更糟。」也正因为这段痛苦的回忆,让翁顺砚希望能够用音乐治愈更多痛苦的人——这才造就了如今这位在剧场舞台上挥洒自如的音乐家。
翁顺砚是幸运的,他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之中找到了救赎;可还有更多的「翁顺砚」并没有这么幸运——有的研究成果迟滞不前,有的黯然退出科研生涯,甚至有的在绝望的折磨中断送了自己年轻热烈的生命。
就像这些案例拼劲全身解数所传达的那样:也许一个优秀的导师未必一定能铺平你的科研之路,但一个恶劣的导师肯定能亲手摧毁你的科研理想。
「科研人的工资补贴都那么低了,就更别为那些不值得的人卖命了……」
这是遗传学家 Joanne Kamens 在开头提到的 Nature 播客中的一句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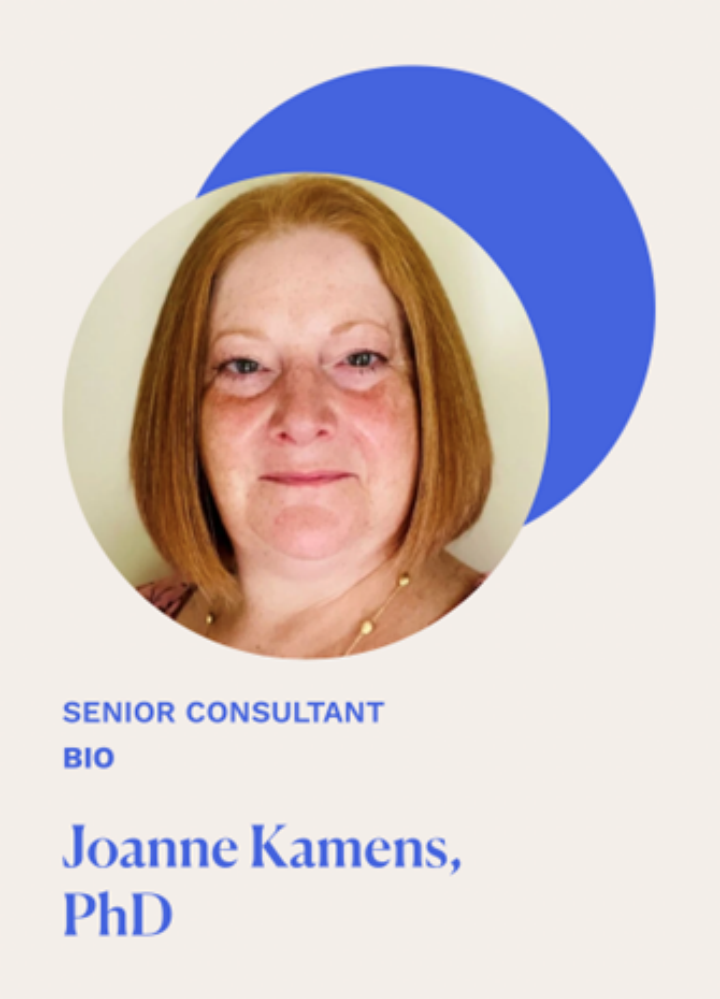
她如今在一家科研咨询机构担任顾问。她认为,衡量是否该进入一个实验室的首要标准,不是实验室规模,不是团队协作水平,也不是工作时间或报酬情况;而是「导师是不是个混蛋」。
否则等待着你的,必然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折磨。
「无论你在哪里从事科研工作,请记住,是你在帮你的实验室一个大忙,而不是你的实验室在施舍你。」
Joanne 说,研究生们必须对选择实验室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意识,别指望运气!「我不希望他们指望自己运气好,我希望他们主动做好自己的选择,否则难免要陷入一段痛苦而低效的科研经历。」
一方面,你的导师应当能够友好地对待你——这应该是底线。另一方面,你的导师应当对你进行恰当的科研培训。即便在未来你未必会以学术为业——只有约 10-15% 的研究生最终会在学术界工作;但你的老板至少应当在这段科研经历中为你提供支持。
「想办法跟实验室里的其他人聊聊,问问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会不会选择这个实验室。如果他们非常犹豫不愿回答……那么就该提高警惕了。」
第二位嘉宾是在 JCB 担任科学编辑的 Tim Fessenden。他在芝加哥大学读细胞生物物理学博士时,进入了一个年轻的实验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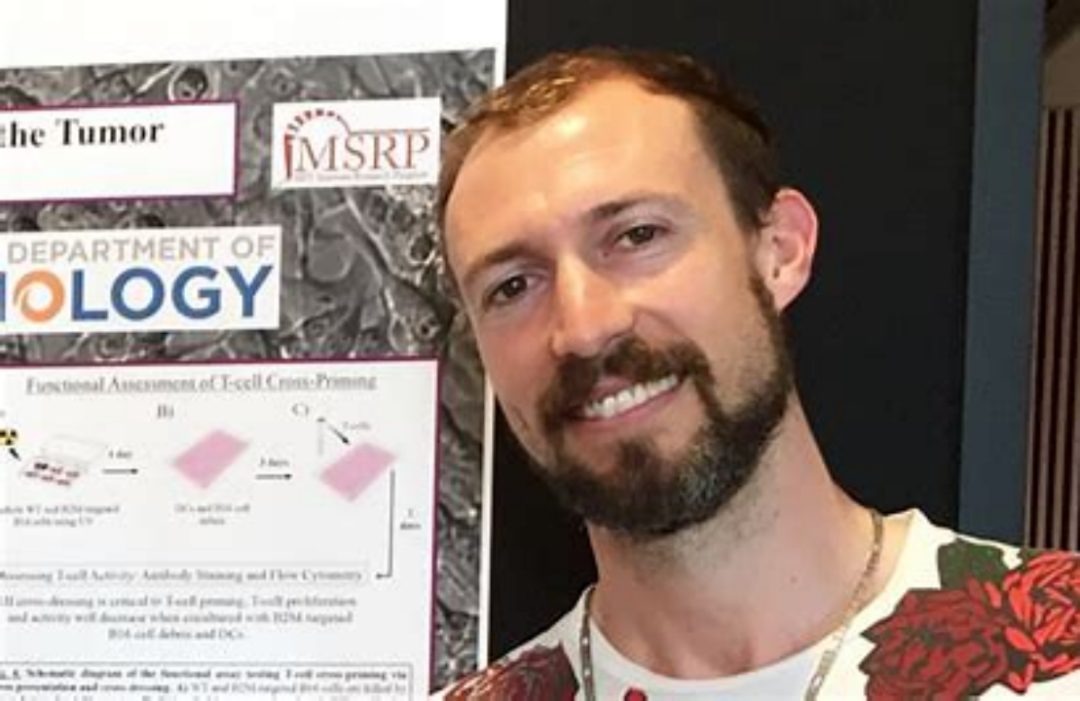
「新实验室确实有众多新项目的广阔视野,以及充足的资金;但同时,你很难确定这些新项目能为你带来什么,导师的指导风格也难以预料。」
「因此,你必须想办法来向这些同样第一次当导师的人提供反馈。这是一种需要研究生和导师共同发挥作用的关系。」
第三位则是在兰道夫-麦肯学院任教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 Kim Gerecke。出于曾经在大型实验室读博的经历,她放弃了进入大型机构的机会,选择来到只有几个人的小型私立学院工作——

「大型机构确实钱多、设备好,但……这并不意味着对你更好。」她说,自己工作五年来,从来没有见到大老板出现在工作台前。
「如果我以后就像他一样,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对公文政务,我又干嘛要在这里学习这些前沿的实验研究呢?」
因此,Kim 表示自己宁愿选择一个导师更重视指导学生的小机构。
读到这里,相信读者们已经从这些话糙理不糙的分享中get到了重点:
一个科研人在未来能否继续走在科研道路上、走上什么样的科研道路,能走多远,很大程度上受到曾经接触到的导师影响。
导师,平台——决定一个博士产出的关键因素
在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下,一个博士的未来的学术生涯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论文产出情况。
在影响一个博士的论文产出多寡的因素中,个人努力占几成?
个人努力确实很重要,但又没那么重要,或者说没有其他因素来的重要。
最近发表在 Research Policy 上的一篇题为 What makes a productive Ph.D. student? 的研究,通过对 2000 到 2014 年间 法国毕业的 77143 名 STEM 领域的博士毕业生的统计研究发现,导师的学术水平,从教时间长短,导师的人脉,拿 funding 的能力等等都与博士的论文产出情况直接相关。

当然,是否高产,科研生涯长短这些都是后话,在进入一个实验室前,最要紧的还是记住 Nature 的这句忠告:别相信运气,看清楚这个 PI 是不是个混蛋!
参考来源:
1.《去美国交换被导师折磨,学了14年的专业一朝放弃…投身公益的他,用音符将爱传递》精英说,2018.02
2. 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d41586-022-01886-7
3. https://www.sciencedirect.com/science/article/abs/pii/S0048733322000853?via%3Dihub
题图来源:站酷海洛
